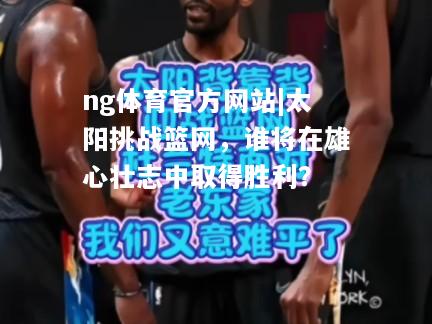
<strong>导语:</strong>历史,ng体育官方网站人民与记忆是ng体育20世纪人类极为重要的三种经验,特别是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讲又尤其重要。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伤,奥斯维辛,南京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这些切实存在的事件共同塑构了20世纪的人类经验。<br/>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以电影为切入口体认历史,人民与记忆。搜狐文化独家整理了戴锦华的思考。上半部分呈现了历史,人民与记忆在20世纪的交错脉络。下半部分重点展现的是1949年之后中国电影当中“人民形象”的变迁消损史。<br/> 文章未经作者审阅。<br/> <strong>作者介绍:</strong>戴锦华,1959年生于北京,从事大众传媒、电影与性别研究。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 研究所,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兼职教授。出版著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中国妇女文学研究》(与孟悦合著),《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雾中风景》,《昨日之岛》等。<!--IMAGE_MARKER_0--> 接下来我ng南宫体育想借助电影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中国,人民形象在电影当中的变化。当然我可以延伸到更长的时段,比如说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的时刻,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的黄金时代,或者40年代中国电影成熟的一个黄金期。但我还是选择了1949年这个政治历史断代的时间作为讨论的开始,因为这段历史是我们迄今为止一段“连续”的历史。<br/> <strong> 一、50-70年代:如何在集体前景下讨论个人</strong><br/> 50到70年代中国电影当中的人民形象是建立在在一组“拯救者-被拯救者”的关系当中。我曾经也用调侃的方式讲过,50到70年代中国电影创造了一种历史断代法,<strong>这个历史断代法以什么为标志呢?就是共产党人的到来。共产党人到来之前是世前史,共产党人到来的时候历史才发生,所以有的地方1921年历史就发生了,有的地方1927年历史发生了,有的地方1949年才发生。</strong><br/> 因为在这些电影当中有一种论述,就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代表的是一种历史的拯救力量,当它到来的时候人民得救了。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喜欢开玩笑,<strong>请问中国哪里天气最好?有两个标准答案,一个标准答案叫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另外一个标准答案叫社会主义的东山坞永远是大好春光的艳阳天。这样的调侃是针对于相对历史断代学的,旧社会是黑暗的、阴霾的,新社会是阳光灿烂的、充满希望的。</strong>比如《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从黑牢里逃出来就一直在黑夜里,走着走着进入到了一个山,山头上有一块界碑,界碑上清楚写着分界岭,翻过去就是解放区,太阳就出来了,阴云就散去了。<br/> <strong>我们调侃的正是这样一种越来越教条化的单一想像,作为拯救者形象的共产党人成为去描述历史的参数。</strong><br/> 《白毛女》、《红旗谱》、《董存瑞》分别出现在50到60年代,其中最后一部是1964年《红旗谱》,而《白毛女》和《董存瑞》都是1955年以前的中国电影,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作,是共和国电影艺术。在这些电影当中,今天我们称之为底层的角色,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当中是绝对的主角,他们是某种制高点和顶层,因为他们是代表国家的主人,代表着历史的命运,代表着人类历史的发动机和动力,这是从宪法到文化表述当中,他们所占有的历史性的地位。<br/> 《白毛女》、《红旗谱》、《董存瑞》这三部电影,如果大家都没有看过的话,我很难一一给大家讲故事了。以《董存瑞》为例,我们会发现人民除了占有绝对的、被仰视的、崇高的,引导视觉的地位之外,其实它们同时联系着一种叙事可能,而在这个叙事可能背后是尝试建立一种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努力。<br/> 董存瑞也罢,潘冬子也罢,小兵张嘎也罢,或者普通的农村妇女红英也罢,他们在电影故事开始的时候都是普通的百姓,在电影当中他们的成长过程是他们接受教育,开始识字,接受一个重要的启蒙——阶级启蒙。<strong>所以人民联系着一个关键词,或者说一个关键想象——阶级意识。这里的阶级意识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第一次开始把你自己的生活,梦想和更广大的人群联系在一起,和一种历史的可能与历史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当你达成了这样一个自觉的时候,你就从一个普通的百姓成为了人民中的一员。</strong><br/> <strong>它背后试图传递的是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一种不同的历史想象,一种不同的政治实践的可能,而在这种可能当中,以阶级为名的人民是占据绝对的主体位置。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想象始终没能处理和解决的一件事,人民与现代社会所创造出来的孤独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如何在集体的社会的前景之下讨论个人。当我们说历史的命运是集体去创造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历史当中的领袖,历史当中的英雄?中国电影创造了这样一种表述的可能:英雄成长的故事。一个英雄从懵懂无知的百姓开始获得了对历史世界的认知。</strong><!--IMAGE_MARKER_1-->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60年代中期的《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党代表洪常青引导吴琼花看地图,问中国在哪啊?吴琼花已经识字了,指着地图说中国在这儿。海南岛在哪啊?吴琼花指着地图说在这儿。那我们叶林寨在哪啊?吴琼花在地图上找不着了。由此说我们在中国的命运当中多么渺小,我们在世界的现实面前多么渺小,但与此同时我们这个渺小的局部是更大视野的组成部分。你可以认同也可以拒绝这样的说教,但它是一个极端形象的过程,表明了人民的历史形构过程,把个人命运和整体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过程,打破空间限定去想象更大世界的过程。而这种连接也曾经在世界范围之内成为真实的连接,否则你就不能想象除了白求恩之外,还有那么多的欧洲人投身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日本的共产党人开着弹药车冲进东北抗日联军的营地,被抗日联军击毙,发现在他的口袋里有一封信,信里讲我是来给同志们送弹药的。<strong>在我们控诉万恶的日本鬼子的时候,这种故事不再被讲起。</strong><br/> 电影《青春之歌》(1959)当中,林道静把自己不幸的个人命运联系到阶级的命运上去。林道静的故事当中包含了另外一个潜在的主题,也是20世纪的一个主旋律式的主题:背叛。这里背叛是指背叛主流与强势,背叛你的利益集团,朝向你的利益集团的敌对营。面对相对你来说的弱势的,边缘的人群,你去献出自己的一切,为改变他人的命运而斗争。这是20世纪的历史当中在全球范围之内普遍发生的事实。大概今天很多人会说那是有病吧。因为趋利避害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但是舍身取义是人类人性的光辉。今天我们要讨论利他主义的时候,要给它一个名词叫做合理的利己主义。利他行为不过是一种合理的利己。比如雷锋,雷锋是孤儿,所以他对亲情有特别大的需求;雷锋长得太矮,所以他有强烈的自卑情节,他特别需要别人肯定他、感谢他。除此之外我们没办法想象一种单纯的利他主义。<br/> <strong>二、八、九十年代:宣共与反共并存的电影叙述</strong><br/> 众所周知,7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进入了重要的转折时期。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简单地理解为结束文革、逆转历史开始新时期的话,就错了,因为文革的历史终结是在今天称之为文革历史的最后段落当中已经开始了。70年代发生了石破天惊的事情,中国向他最大的敌人伸出了橄榄枝,世界上最臭名昭彰的右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际上在那个时刻冷战结构已经内在解体了,不久以前我听到一个美国历史学家说,那个时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苏联解体,这个说法当然有点夸张,可是这种互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的。<br/> 80年代的中国社会非常有趣,它是50到70年代历史的延续,包括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依然存在,但是同时所有的变化都在体制内发生,直到某一个时刻它如滴水石穿一样冲破原有的结构,整体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与历史。<strong>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作为第五代的第一批年轻导演遗世而独立,突然登上中国舞台和世界舞台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艺术、世界与审美,想到的是让西方看到中国,同时他们仍然历史性地携带着他们曾经成长的构造记忆和价值。</strong><br/> 我选择1985年《黄土地》作为第五代奠基的代表,第一次走上世界并震惊世界的新中国电影。我非常不喜欢近年来陈凯歌的创作,甚至可以说我极度厌恶这些创作,但是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修养使我仍然坚持《黄土地》是最优秀最重要的中国电影之一。<!--IMAGE_MARKER_2--> 而当我们今天从人民的角度反观《黄土地》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第五代的造型,第五代的摄影机位置的选择,第五代所创造的非常规性的,非完整性的构图,第五代向世界打开的一个用摄影机所呈现出来的空间化的历史和时间之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黄土地》当中有四个角色:共产党的文艺兵顾青,他住到了陕北贫困山村的一家人当中,这家人当中包含一个老父亲——翠巧爹或者憨憨爹,一个是姑娘翠巧,一个是儿子憨憨。每一个人都在故事中占据着叙事主体和历史主体的位置。作为共产党军人,顾青当然代表着当时仍然是官方的历史叙事当中的主体位置,但是翠巧爹在这个故事当中绝不是愚昧的农民,他代表着在土地上艰难生存的人们的顽强和智慧。在翠巧的故事当中,翠巧爹就是封建家长,但是翠巧爹给顾青唱了一支歌,表明他比谁都明白女儿的命运,他比谁都同情女儿的命运,但是他无从改变的是这个世界的结构,而翠巧代表着五四以来的主导叙述:最底层被压迫的妇女,她们是最激进的变革力量。20世纪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战斗革命的呼喊,最先站出来的一定包含大量的妇女,因为她们的命运最直接的应对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命运的描述:失去的只有锁链,得到的也许是整个世界。她们是最没有可牺牲的东西,而她们最可能去赢得新世界的这样一群人。憨憨代表着五四以来另一个强有力叙述:青年的变革力量。<br/> <strong>这个故事当年曾经被英国《卫报》称为共产党宣传片,一方面它赢得了很多世界声誉,但是还被称之为共产党宣传片,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好像有一个很典型的故事,共产党作为外来人进入一个山村教化他们。但同时这部电影也被视为反共电影,为什么?因为和50-70年代电影最大的不同是,这个共产党人的到来什么都没做成,谁的命运都没改变。</strong><br/> 在电影当中翠巧显然是一个暗示,翠巧爱上了这个外来人顾青,这其实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故事,一个外部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希望。翠巧穿上嫁衣把自己嫁了,她追上顾青说,顾青大哥我跟你走,<strong>顾青的回答是我不能带你走,双重规矩:庄稼人的规矩,宗族社会的规矩使得顾青不能带走翠巧;公家人的规矩,共产党军人的规矩使他不能带走翠巧。所以他给翠巧一个承诺:我再回来。但是电影最后翠巧对弟弟说姐等不得了,所以她自己剪了头发自己摇船过黄河。</strong><br/> 在电影当中,连个漩涡也没看到,翠巧就消失在黄河里了,黄河依旧东流去。而同样由于顾青到来唤醒的改变命运希望的是憨憨,电影最后一个段落是憨憨三次逆人流奔向顾青,但是当憨憨终于奔出去了,镜头反打:辽阔的地平线上什么人都没有,而且顾青迎着人群走来的画面当中,地平线是倾斜的。当憨憨冲出人群奔向顾青的时候,地平线变成水平的了,但是顾青不在了。由此说这是部反共影片,因为共产党没能带来解决,没能带来希望。我认为这部电影今天的意义刚好在于这两种极端的评价,在这部电影当中你看到了历史的巨大力量和遗产。<br/> 我记得《黄土地》剧组结束拍摄的时候,陈凯歌回到电影学院给大家讲创作经验,他说再一次到达黄土地的时候,我们太震动了,<strong>黄土地上的人们是没吃没喝唱欢乐,我们这些人是有吃有喝写烦恼。这不仅仅是一个感悟,他们普遍下过乡进过厂扛过枪,他们曾经真切地和人民与土地在一起,这个东西构成了文化研究上叫做structure of feeling (情感结构),对于土地与人民的那种由衷的尊敬是身体性的。</strong>《黄土地》之中摄影师张艺谋所拍摄的翠巧爹的特写镜头,当时的人们一眼都能认出来,他在重复一幅著名画作就是罗中立的《父亲》。当你把两幅作品放到一起的时候,对照着此后的绘画小说音乐电影,你会看到那份敬意,这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这是一个情感的选择,这是一个历史结构的显影。<br/> <strong> 三、21世纪:“人民形象”基本从电影之中消失</strong><br/> 首先是贾樟柯2000年的《站台》,在《站台》当中主要人物并不是劳动者,但他们是小县城当中的小人物,底层的普通人。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站台》的主题的话,就是底层人的生命像芦苇,蒲草一样柔韧,但是他们只能随风摇动,随风而去,他们只能不断地被历史社会和命运所拨弄。劳动者和劳动场景偶尔出现在荧幕上,比如说王全安拍摄的《纺织姑娘》(2010),电影中是工厂与工人,影片的空间仍然不时唤起我们对50到70年代的工业题材电影的想像,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会不断打破这种想像,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位纺织女工绝对地处在一个无法自主命运的状态当中,她绝对的无助,绝对的弱小,绝对的边缘。<!--IMAGE_MARKER_3--> 后面的一批电影就不用说了,比如说《二十四城记》(2008)、《美姐》(2013)、《推拿》(2014)都是我尽力想去呼喊支持的电影,在这些电影中就特别痛切地感到:<strong>人微言轻,无权无势者的呼喊是多么的无力。</strong>那么在《梅姐》当中我说久违了的中国乡村生存,在《推拿》当中我说久违了的社会真正的弱势之中的弱势,因为它们不仅边缘底层还残疾。那么在《推拿》当中我感动于导演不仅把他的摄影机朝向了这些边缘的人群,而且他在整个电影的叙事技巧、摄影语言当中,<strong>考虑到了一个电影的挑战也是社会的挑战,电影的挑战就是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如何呈现没有视力的人群?社会的挑战是当你挟有资本,可能是大资本可能是小资本,《推拿》肯定是小资本,你狭有小资本,你掌握专业技术,你手持摄影机进入了一批无权无势,甚至没有视觉能力的人群的时候,你如何不是强势的?如何不是暴力的?你如何不让你的摄影机去强暴他?</strong>电影做的并不完美,但是它高度自觉而且充分努力了。我坐进影院的时候第一分钟我傻了,我说这电影怎么这么笨呢?一边打字幕还一边念字幕,等我明白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如果你想一想也可能有一些观众是盲人,那些电影中出演的盲人演员们也坐在影院里,他可以听到他的名字被念出来,他就可以去想像电影的剧情开始了。<br/> <strong>而今天在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回瞻当中,所有的苦难都变成了洗礼,人民的形象依旧光辉,但是人民的形象已经渐渐和国家民族的概念等同在一起了。而在中国电影中人民的形象基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种试图占据多数位置的修辞,比如小资,中产, 80后、90后。</strong>在我参与的一个会上,一位对中国电影生产有一定影响力的人说,居然让我们为多数人拍片,他说这太激进了,我们只为90后拍片。我当时就无语了,因为他的这个表达本身违背了资本逻辑,只为90后拍片就意味着未来的资本空间就局限在90后,纳入了80后就是更大的资本纵深。这个让我耿耿于怀的小例子告诉我们说,90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阶层,集团,社会群体,他们开始占据和盗用了多数的民意,尤其对于今天中国电影来说,他们最真实的身份就是消费者,他们盗用占据了社会主体的位置。<br/> 而曾经作为社会国家主人公的那个社会群体,就被这个小群体逐渐排斥出了中国荧幕,他们偶尔的出现在艺术电影当中。所以今年中国电影市场反复强调说,艺术电影是反电影的、小众的、无趣的、丑陋的,为此就给它0.9%到1.5%的拍片,把90后所欢迎的大众电影给它59%的拍片。如果你偶然走进影院想看电影的话,能看见的只是那些为90后拍的电影,而没有明确的为90后所拍的电影。如果说他们偶然把视野朝向了中国的多数,朝向了今天仍然在真实的物质生产当中劳作的人们,这些电影就小众了。<br/> 整理编辑:王远哲<br/> 更多内容请扫下方二维码 打开搜狐手机网文化频道或搜狐文化微信公众号<!--IMAGE_MARKER_4--><!--IMAGE_MARKER_5-->

发表评论

暂时没有评论,来抢沙发吧~